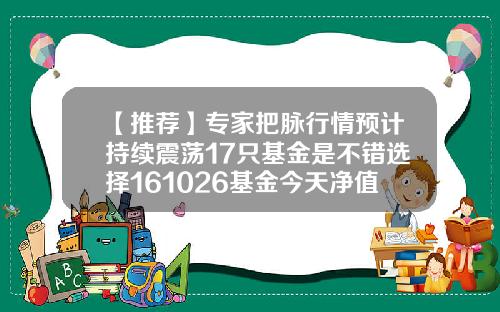吕梁铝合金门窗加工工厂地址
文章目录:
1、赤泥堆场变绿洲——吕梁铝协走访兴安化工赤泥堆场纪实2、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3、“粽”出小康路——吕梁山区“粽子村”的逆袭故事
赤泥堆场变绿洲——吕梁铝协走访兴安化工赤泥堆场纪实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入夏以来,人们惊喜地发现位于孝义市辽壁沟的兴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化工)赤泥堆场上面冒出一块“绿洲”。昔日寸草不生的赤泥堆场,现在树木成荫、芳草丰茂,天鹅戏水、喜鹊欢歌,麦苗青青,迎风见长,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近日,吕梁市铝行业协会一行人来到兴安化工进行走访活动。
兴安化工是2008年孝义市政府招商引进的一家大型氧化铝生产企业,总投资100多亿元,年产氧化铝300万吨,是国家工信部认证的绿色工厂、山西省百强企业、山西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2021年上缴税金4.81亿元,居孝义市企业第三位。自投产以来,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771亿元,上缴税金近80亿元,为社会捐赠7476万元,给孝义市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赤泥堆场是氧化铝企业不可缺少的配套项目,为保证企业的安全运行,2008年兴安化工在距厂区11.5公里的辽壁沟投建了赤泥堆场项目,设计总库容6009.68万立方米,总投资5亿余元。
大多数人不知道赤泥是什么?但大家都知道铝。铝在我们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从铝制的锅碗瓢盆、易拉罐、铝合金门窗到飞机、游艇和汽车上的铝合金材料等到处都有它的身影。赤泥就是铝冶炼工业中产生的一种碱性工业固体废物工业,简单来说,铝土矿与碱性物质发生反应,分离出氧化铝和赤泥,氧化铝经过电解后生成金属铝,因赤泥中含有大量的Fe2O3呈现红色,习惯称为赤泥。目前平均每生产1吨的氧化铝,就会产生1~2吨赤泥。
相较其他固废,赤泥碱性高,成分复杂,综合利用难度大。截至目前,尚未有经济有效的大规模处置及综合利用技术,致使全球利用率不足10%。
大量的赤泥不能有效利用,只能堆存。吕梁铝协了解到,我国95%的赤泥采用露天堆存的方式处置,堆存占地面积达12万亩以上。较为常见的赤泥堆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湿式堆存,将泥浆状的赤泥利用管道输送到堆存场地,沉降后的上清液到氧化铝厂回用;另一种是干式堆存,将赤泥洗涤、过滤后添加增塑剂,降低赤泥浆液的黏度后进行堆存处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氧化铝企业采用干法堆存处理,其处置成本约占氧化铝产品产值的5%。
赤泥会令民众因对它不了解而产生顾虑,即赤泥有没有放射性?有没有污染水源的重金属?
吕梁铝协调研数据显示,通常赤泥的pH值为10.29-11.83,氟化物含量4.89mg/L-8.6mg/L,按《有色金属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5058-85),因赤泥的pH值小于12.5,氟化物含量小于50mg/L,属于一般固体废弃物,而不是危险固体废弃物。但是,干式堆存的处置方式需要占用大量农田、土地,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赤泥除含碱量高外,还含有铝、铁等金属元素,堆存过程中如产生渗漏进入地下水、地表水等水体,可形成沉淀物、悬浮物、可溶物,造成重金属污染,水体的pH值上升等不良生态影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兴安化工多年来深入贯彻落实铝工业“绿色”发展理念,赤泥堆存采用皮带输送为主、汽车运输为辅的干式堆存方式,边堆存边复垦,为辽壁沟造平原、打梯田,在赤泥堆上植树、种草、种小麦、建池塘、搞养殖……截至目前有效库容200多万立方米,累计复垦投入4000余万元,完成复垦1032亩,正在复垦450亩,改变了赤泥堆寸草不生的“传说”,在赤泥库上造出了一片绿洲。
“本次走访受益匪浅,感触颇深,我们吕梁铝协将继续致力于服务全市铝企健康可持续发展,倡导氧化铝企业积极寻求赤泥综合利用有效途径的同时,加大力度做好赤泥堆场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改善赤泥堆场生态环境,真正践行铝行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理念。”吕梁铝协会秘书长高永明说。
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多雨的北京秋日,贾樟柯坐在美术馆后街的一处文化创意园区里,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是他母亲,他说汾阳话。这让我想起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的情景,周围是不冒烟的烟囱和不再生产的红砖墙面厂房,还有汾阳话营造的“街道生活”。方言和相似之物复制了遥远的“附近”。
“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口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这是贾樟柯的提问。多年前,他想走电影之路的源头是因为看了《黄土地》,这是一部有口音的电影。在那之前,普通话几乎统一了中国电影。那是一个寻根的时代,也是先锋的时代,“寻根”仿佛是返回土地,“先锋”则像是面朝海洋。贾樟柯的新片不止于此,时间向两端延长,原本是《一个村庄里的文学》,到最后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的拍摄地点从陕西到了山西,再从河南到了浙江,土地朝向了海洋。
“电影里说方言了,才有了个人化的表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口音,从说方言的贾家庄人和贾平凹,过渡到带浙江口音的余华和带河南口音的梁鸿,然后落在讲标准普通话的梁鸿儿子身上。口音从电影上的统一,散播到现实的差异,最后在现实中又逐渐失去了丰富性。
余华部分的拍摄场景,贾樟柯没有选择小桥流水人家,而是选择了铝合金门窗。他在汾阳和海盐之间寻找着相似性和日常性。同时,他又在农民的粗粝生活中,激发诗性。他和同事们摘抄了很多诗句,让村民们去挑选有感应的句子,喜欢哪一句就读哪一句,比如“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我不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可以是每个人的。”贾樟柯说。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余华
在浙江海盐,影片拍摄的尾段,贾樟柯的团队本想上午去拍海边,但发现海面发黄发白,并不好看。他们等到天黑,水起来了,浪起来了,海水的颜色都变了。摄影师手持镜头跟着余华在海边走,贾樟柯在摄影机旁跟他聊天,余华讲了那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贾樟柯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电影的名字。
这是全片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也变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镜头朝向海洋,似乎没有止境,明暗莫辨的电影和现实深处,不确定,也因此蕴含未知和可能。
作家与乡村
人物周刊: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很少集中地看到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想到拍他们?
贾樟柯:我们在拍摄之前,基本上确定了是从马烽讲起,然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这样一个结构。最终确定拍摄的时间确实跟吕梁文学季有关,因为在一个村庄里,突然来了四十多个作家,他们会谈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不管是贾平凹老师也好,梁鸿老师也好,他们成为作家之前就是农民,然后都是通过考大学变成了城市里的人。他们的写作一直也都围绕着乡村经验在进行。余华是小城市的,我也是小城市的,我知道小城市跟农村是很紧密的,有这样一种关联。
再一个跟年龄有关。贾老师是50年代生人,余华老师是60年代的,梁鸿老师是70年代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群像的接力关系,可以接力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无非通过两种人:一种是当事人,还有一种是观察者。他们的身份本身既是当事人又是观察者,我就觉得为什么不用他们来讲述?包括他们的语言色彩和概括能力,对于细节的把控都是超强的。作家天生就是说书人,他们就是传递人类情报和消息的人,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敏感,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胜任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贾平凹
人物周刊:电影拍到70后作家为止,更年轻的作家,比如80后作家,为什么没有考虑拍进来?
贾樟柯:70后和80后作家基本是城市的一代了。我们的主题是乡村经验。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跟乡土有密切的关联,但确实是在转变。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经验也能看到乡土的影子,但毕竟是建立在城市空间里面的。
人物周刊:电影里看到了变化的汾阳。你说过,汾阳身处城市和农村之间,连接着两者,汾阳现在是更接近于城市了么?
贾樟柯:从空间或生活方法上,汾阳确实城市化得厉害。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都有变化。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是它的人际结构相对还是稳定的,比如说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相较于大城市,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也会奔波于各种亲戚家的满月酒、婚礼、葬礼。他们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另外一种人际结构。这个人际结构不因为人的移动而改变,因为人也会移动回来。大部分的家族聚会都不是发生在大城市,都是发生在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其实也不大。我自己在北京几乎没有亲戚,我是没有这种生活的。小城市还是保留了这种人脉关系,血亲在那儿。
方言与口音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的电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说方言的,大家跟世俗生活仿佛是脱离开的,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你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电影里边的人,基本上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贾樟柯:对,过去的电影普通话时代造成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用第二语言来表演。我自己很喜欢用方言,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自己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涉及传达信息和情感表达,我就是山西人的思维,用的词语都是山西话,我很难用普通话的思维来想一个电影。比如说,表达爱情可能就是“我爱你”,多尴尬的一个事情是吧?山西话就有很多技巧,很多独特性。广东的思维模式可能就是粤语的方式,大家是不一样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梁鸿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老师的儿子不太会说方言了,她一句句教他,你是不是对方言和口音特别敏感,所以拍了下来?
贾樟柯:梁鸿和她儿子在那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预判,我觉得可能父母都是很正宗的河南人,在家里面,夫妻应该也都是说河南话,但有可能小孩不会说。我怀着这种好奇去发问,果然是这样子的。
方言的问题挺复杂。我发现不会说方言,大多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好像还可以。广东人和上海人说方言,很骄傲的,所以他们能比较好地保护。欠发达地区有文化信心的问题。特别是上学读书以后,基本上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融入到普通话的行列里。
人物周刊:在汾阳存在这样的问题么?
贾樟柯:我在汾阳就经历过挫折。我拍一个电影,去勘景,问路正好问到放学的中学生。我说非常标准的汾阳话,小朋友回答我时用普通话,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汾阳话的异乡人。在电影界,方言被认为会影响票房,因为很多观众确实还不是太习惯看字幕,还是要直接能听懂。过去,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认为方言是妨碍市场的。你听我们汾阳话,那就跟听外语差不多。
人物周刊:电影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故土的独特感受和国际化之间,艺术上的考量会有一个变化么?
贾樟柯:这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回到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应该带有导演自身的基因、血脉、优点、缺点、口音。我跟白睿文有本书就叫《电影的口音》。如果你秉承的是一个作者论的创作方法,不是一种类型创作,这些事情就想得不多了,我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一些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国际观众是不是能欣赏?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困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电影语言,高度的电影语言自身就是国际化的。局部的不理解一定比比皆是,但是电影还有结构,还有影像,这些是更容易被更多人理解的东西。
土地与海洋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影片的名字,从黄色的土地,到蓝色的海洋,从陕西到山西,从河南到浙江,最后出海了。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最初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后来改了名,是在余华老师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个意象对我来说,意味着开放。海洋是一个现代化的符号。你看时代里的作家其实有内在的眼睛,有进化,一代一代地进化。
比如马烽先生,经历了社会改造和集体化,向土地要粮食,他是这种大的社会运动中的作者,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到了贾平凹老师,就逐渐个人化了,到了余华,完全就个人化了,到了梁鸿老师,就私人化了。这里面有一步一步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人在现代化。
贾樟柯与梁鸿对谈
这个电影已经拍出来有两年时间,我拍的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世界确实已经在重组之中。那时候主要是科技、互联网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颠覆。接下来加上疫情,又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巨变,整个世界变得如此的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这个电影,有两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是回头看,往往我们需要回头看,是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我们要看一下来时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不确定里头,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我们具体的路径都不知道,世界的演化也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离开也不知道,全球化是不是还会恢复,还会变成过去的那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去坚信的,就是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我期待的东西,或许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它没那么容易,没那么顺利,所以要四代人在这里面接力。
疫情与重组
人物周刊:这两年的疫情,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贾樟柯:我觉得一方面,疫情很直接地带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衰落,这个衰落本身还是很剧烈的。你拿文化来说,疫情之前,你看北京有多少演出,有多少外国的剧团、展览、人际交往。文化交流曾经这么密集,但现在很少了。
另外一方面,疫情给互联网生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上网课,已经习惯了网上开会,已经习惯了远程的工作。它的不确定性是,世界重启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疫情的封闭性跟互联网趁虚而入带来的颠覆性的生活方法,确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对你的具体影响是?
贾樟柯:拿电影来说,电影天生是一门全球化的艺术。最初电影有个外号叫“铁盒里的大师”,因为它是超语言的,电影在默片时代不需要语言,所以它能横行世界,带来了借由电影的全球化交流沟通的趋势。但是,它也因为疫情中断了。未来我们都在互联网看电影?是不是主流的观看方式会逐渐变成这样?重启之后,很多事情是回到过去?还是有变革?我觉得它确实是处在一个不确定里面。包括我本人的精神跟思想,其实也在一个重组的阶段。我两年没有拍电影,我觉得不应该着急去拍,因为思想不稳定,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出入很大。
人物周刊:出入有多大?
贾樟柯:就拿我们电影的播放媒介形式来说,今天我可能觉得电影是唯一的媒介,最符合电影特点的媒介,就是影院放映,就是大银幕放映。因为聚众是很重要的,集体观看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放大是很重要的。几十米宽的银幕把一张脸投射下来,我们回到电影最初发明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影像可以这样。你第一次看一个特写镜头肯定是吓一跳的,有这种感受。但第二天我就觉得这可能不重要了,电影已经一百多年了,iPad看也可以。我也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我也不确定。
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要坚持大银幕先放映,再流媒体放映?所以,我们拖了两年。如果流媒体放映,早就放了。两年里面,一会儿电影院开,一会儿不开,给很多电影造成困扰。我在思考我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保守或开放的人,我觉得我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还是说我这个保守是对的,我应该去坚持?
人物周刊:如果失去某种聚众观看的形式感,电影还是电影吗?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人类有很多仪式都失落了。过去我们有很多仪式,很多祭祀,我们肯定在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拜天拜地,这些东西。但是消失也就消失了。生活、科技、人类在演进。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些唱挽歌的人?我想这个就好像京剧一样。在京剧最活跃的晚清和民国时代,当它衰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可能跟今天的电影一样,大势你无法阻挡,这时候就考验个人,你是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退出与继续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平遥电影节?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
贾樟柯:当时想不做了,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做太多年,因为我的主体工作是一个创作者,我是写剧本和拍电影的。办电影节是一个服务业,服务影迷的一个工作。它很重要,但我是不是要用很长时间来承担这个角色?在第一届开幕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策展人。因为我们国家电影策展是一个空白,我们请了国际的团队,我们希望自家人能成长起来。我从创办之初,就在想怎么脱身。
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招商、选片都广受好评,那时候就萌生退意。但是这之后你发现你暂时还退不了。确实,平遥电影节借由我的资源比较多。我以为可以脱手,但是好像一下子不干了就有很多问题。那就继续再做几年。下面又继续再走一段路。
去年就是真的不想干了,我觉得我该拍电影去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很成熟了,他们可以做。团队很好,商业反应、市场反应很好,但是转化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我一直担任桥梁作用,好像我走了就把梯子给抽走了,两边接不上了。
平遥电影展非常正常,10月12号第5届就举办了,目前为止,筹备都很顺利,选片质量也很高。文学季我们的编制和人员还在,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应该今年不会办了,希望明年能继续。
人物周刊:又是电影节又是文学季,到这个年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热情去做这么多事情?
贾樟柯:其实电影节跟文学季,我都是想带一带,然后可以良性地往前走。因为我喜欢这些事情,这些活动它能给行业、年轻人,还有观众、读者带来一些收获。过几年成熟了,我就离开了。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比如说文学季也好,电影节也好,确实是因为这都是新兴的业态。我觉得我确实是个专家,我没办过电影节,但是我一年四季在参加电影节。我觉得这方面没人才,我自己还了解一些,那我自己办呗。很多年轻孩子现在学策展,这些人成长起来,他有他们的能力、脉络之后,不需要我们导演去办电影节,人家策展人去办电影节,何必你一个导演去做呢?实际上导演办电影节的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第一届影展,主要的会议是在介绍什么是电影节?电影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这么一个电影展?就是从这个开始讲起。这是集我二十多年参加电影节之观察,心血放在这上边,就是天天上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太原中秋特别放映现场合影
人物周刊:你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觉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贾樟柯:比如说等级制度。国外的电影节等级森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平遥电影节就是一个平等的电影节。我们平遥电影节来的人,都可以济济一堂,就没有那些等级。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普通观众,他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很短的。国际电影节,你去试试?
人物周刊:等级森严到什么程度?
贾樟柯:所有的细节。从你出门机票的舱位,到你下榻酒店的待遇,到你的权限。我记得带同事去国外电影节,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反对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电影节,它有很好的口号,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我们也会讨论,电影节是不是要用一种煽动“革命”的方法来办?你把他们煽动起来,你又没有服务,你又没有组织,对年轻人成长是好还是不好?电影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公共平台,它是信息交互,它的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在考虑和你电影节所倡导的、和电影的总体策展的观察之间的矛盾在哪里,统一在哪里,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当然也看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优点。比如说媒体系统。办得好的电影节一定是媒体系统最发达的。因为电影节展不单是一种展映聚会,不单是行业,它更主要是通过媒体要把文化成果、观念、观点,介绍给更多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戛纳电影节?因为它的媒体系统。我们的一部电影去法国戛纳一放,印度马上就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尼泊尔也知道了,甚至不丹都在买这个电影,这就是媒体的系统在发生作用。
另外一方面是评论体系。比如戛纳电影节一放,全球重要的媒体评论很重要。英国《卫报》怎么评论?《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借由这些获得来自全球的评价,然后带给电影全球的普惠,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电影节都是国际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是传播不出去的,国际不知道这些电影。那么人家为什么就可以一个首映马上享誉世界?是它的媒体在发生作用。
比如我们好几届电影节,法国《解放报》都给了五六个版,整版整版的。后来我们有一年就做了一个“平遥电影展在巴黎”,我们带了6部影片去,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影片在法国产业界已经有一些知名度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些影片全部卖出法国版权,我觉得这就是成果,走出去就是这么走出去的,不是自己带着片子放一场就走出去。
现代与转型
人物周刊:我觉得包括电影在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游向蓝色”的那种状态。
贾樟柯:就是开放的、多元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理想社会。
余华
人物周刊:余华的那一部分,他更多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讲述,这跟许多人头脑中某种模式化的“江南”不太一样,当时为何选择这样的拍摄地点?
贾樟柯:其实我们对每个地方的空间是有预设的。一想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河流、庭院、亭子。我去了海盐之后,觉得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海盐有一个公园,就跟苏州园林那样美。
但是我更加发现,海盐跟汾阳差不多,我想我还是拍这个差不多的吧。因为大多数人不去那个公园,它已经是一个遗留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日常。余华的小说都在讲我们的日常,市井生活和世俗社会,那干嘛放到一个那种非常风格化的古典园林里面去拍摄呢?我就选择了那种没有差异化的空间。这些地方并不是说它的风景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地方它有人的风景,它最大的风景是人。
比如卷闸门,90年代以后横行中国,大江南北都一样,你也理解这种趋同化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铝合金门窗,这种空间构造上的趋同化,不妨碍他(余华)在他小说的空间上,有他独特的组织。每个人的美学选择都不太一样。
如果我去拍海洋,我也能拍出一个江南的海洋,它也存在,只是那一部分可能是我不太在意的,或者说我不太强调它。我更强调的还是日常化。我们每天是在园林的假山假水里面生活,还是在铝合金门窗里面生活?我们肯定主要在铝合金门窗里面溜达。
人物周刊:我走在汾阳街头的时候,也发现那里跟全国其他地方像是一样的。
贾樟柯:没了,已经没了。比较大的变化就90年代。我们拍《小武》那年,正在拆。拍完之后,就统一地变成新楼,楼都是6层楼,底下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都变了。过去那些老房子大都已经消失了。许多地方都一样,只是走进巷子里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周刊:汾阳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教堂那个钟楼,还有汾阳中学,有很强的历史感。
贾樟柯:汾阳县城是明代的县城,但汾阳是秦代就设县了,它很古老。汾阳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跟几个元素有关。其中一个是汾阳中学,是教会中学,跟教会有关。一个是汾阳医院。中学和医院给这个县城带来新的教育、新的科技、新的医疗,对汾阳的文化重新塑造还是很重要的。
在汾阳,大多数汾阳人都会跟你娓娓道来汾阳中学的历史。每一任校长是谁。我们第一任校长恒慕义是汉学家,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我上高中的时候,美国大使(恒安石)经常来,因为他出生在汾阳,我们的教务处就是他家,他每次来都带一些电影,带个放映机,带些礼物。
人物周刊:这些对你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樟柯:有。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世界不远。
人物周刊:当初你说想走电影这条路,是因为看了电影《黄土地》?
贾樟柯:我高考没考上大学,我父亲很希望我读大学,但我数学特别差,那时候艺考生不考数学。艺考里面,什么音乐、唱歌、拉乐器,我都干不了。美术可以现学一学,所以我就去学美术,准备用艺考的方法念个大学,满足我父亲的需求。我觉得不是我的需求,我不想读书了那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黄土地》,喜欢上电影。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你重新思考你生活的地方?
贾樟柯:往往我们喜欢一个艺术作品,是经过两重过程:一个是熟悉,对这个生活有共鸣;再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代表着新的角度跟新的发现。好像《黄土地》,一定提供了我对于这个土地从来没有过的理解,所以我才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在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我在想,作家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一开始是从吃饭开始拍,拍的是普通老百姓,这是什么想法?
贾樟柯:这四个人(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笔下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我电影开头交代的。因为这四个人毕竟是四个个案,但是他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历史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从这样的起点来谈起。这个结构实际上延续了《江湖儿女》的结构,《江湖儿女》开场是一辆公共汽车,很多人,逐渐聚焦到女主角身上,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当然《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有更多的面孔,更长的篇幅在讲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最新的拍片计划吗?
贾樟柯:有。有好几个新剧本,但是不会仓促拍。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稳定,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也不确定。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哲学价值观,我想等一等。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才会遇上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确定阶段,不着急表达。得去想一想,随时可以拍。
人物周刊:《在清朝》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好像每次采访都会问起。
贾樟柯:拍摄计划基本上完善了,我们所有的兵器都打好了。
人物周刊:这是在拍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转型?
贾樟柯:对,最初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你的所有电影,总的主题都是转型?
贾樟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百多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里面。
卫毅 实习记者 方沁
“粽”出小康路——吕梁山区“粽子村”的逆袭故事
新华社太原6月12日电(记者魏飚、王劲玉)三片粽叶交错相叠,绕着左手大拇指来上一圈,形成一个漏斗形状,把早已泡好的糯米和蜜制的黄河滩枣塞进去,粽叶封口、马莲草系紧,一个个精美的粽子就成形了……临近端午节,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前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近几年,这个曾经的贫困村被小小的粽子改变了命运,村民靠包粽子、卖粽子脱了贫,走向小康之路。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3岁的村民王金莲动作麻利,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15秒。“现在每月能挣上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打工挣钱不少,还方便照顾家里。
前青塘村位于山西吕梁临县县城以南8公里,湫水河西岸。与一般黄土高原山区村落普遍干旱有所不同,前青塘村有俗称“海眼”的泉水,一年四季水量充足,天然优质的水资源,孕育着400亩品质优良的茂密芦苇。但是,过去守着好资源,村子却没富起来。村干部说,过去芦苇大量卖给了外来商贩,价格很低,挣不上钱。上好的糯米和黄河滩枣,包出的粽子多是村民自己食用。
2015年8月,驻村干部来到村里,与村干部商量,决定利用当地优质水资源和芦苇叶,将“粽子”作为脱贫的主导产业。不过,村民心里打鼓,一个季节性如此明显的产业能否挣钱?
2016年,村干部邀请在外经商的张新勤回村创办粽子加工厂,试水的8万个粽子销售一空。在张新勤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加入这个行业,家庭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从2017年的10多户,发展到今年已经有80多户。全村2500余人中,有近1000人从事粽子相关工作。
村民刘继兰的粽子加工作坊,一年的销售额达到40多万元。去年,她还开启直播卖货模式,销量大涨,粽子的销路越来越广。
如今,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越来越高,粽子也从季节美食变成四季食品。今年青塘粽子产量预计2000万个,销售额预计5000多万元,带动当地村民人均年增收六七千元。
粽子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变化,还凝聚了人气,改变了风气。“以前外出打工的村里人都回来了,家家户户忙着靠手艺挣钱。”前青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鑫说,2000多人口的村子现在没有一个告状上访的人,全都琢磨靠粽子增收致富。
前青塘村还根据资源优势,把苇子工艺品编织、水稻种植、鱼塘垂钓、特色民居旅游、农家乐确定为支柱产业。村里来了不少游客,村干部说,粽香不仅是粽子本身的味道香,吃粽子的人更想吃到“可以回忆的味道”。在前青塘村食品公司的粽子生产车间,几十名妇女穿着工作服,泡好的大枣和各类米堆放在大桶里,透过玻璃窗,购买者看到的是像自己孩童时母亲包粽子的场景。
在村子的不远处,粽子产业园即将建成。“明年粽子产业园建成以后,年产量预计能达5000万个,利润能达6000万元,受益的村民会更多,也将为村里乡村振兴奠定很好的产业基础。”李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