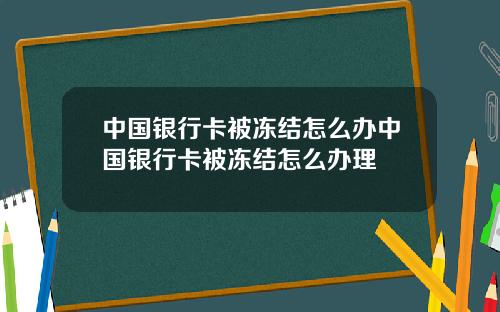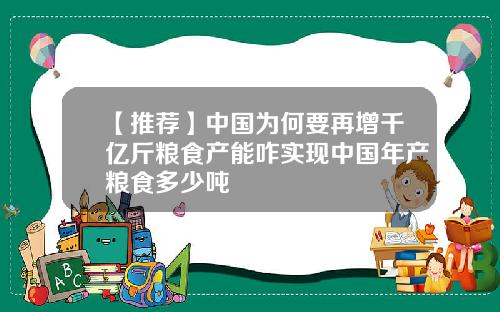从郝家契约看民国长治
这就是30张契约的珍贵所在。在它的解读中,一个完整的店上郝氏家族“耕读传家”的奋斗历程,将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数千年对土地的不离不弃
清末民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
清末民国,也是距离我们最遥远、最模糊的朝代。
它经历了大清王朝由盛及衰、直至灭亡,见证了中华民国诞生、发展、衰败过程,有危及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和逐鹿中原的解放战争,直至作为代表没落势力力量“国民党”“蒋家王朝”被迫“退守”或者“流亡”台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主体政权更替已成定局,等等若干时期。更因为作为这一时期的执政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由于其施政方针的背离人心,以至于在代表群众利益的先进党——中国共产党面前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在政治上远离了大陆民众的天空,走出了中国农民的视线。因而,它最近,但是,它最遥远。
农村,作为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处于封建、闭塞、保守,甚至可以说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时代对外界“愚昧无知”的太行山区晋东南农村,乃至建国初期的太行山农村,同样,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起到了支撑当时统治阶级社会架构无可替代的作用。农业反哺工商业,在这一时期体现得非常明显:“地是刮金板,房为避风港”,农村中的土地、房舍等工具或资本,成为农民“物化”生产资料的全部,是旧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的时间内,直至现在,可以说,仍然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托。
“出入相告,疾病相扶持,守望相助”,这是中国田园牧歌的向往。在这个想往中,守住土地,是对家园最大的守望。何慧丽言: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体现为土地问题的农民问题;百年中国的社会运动形式(战争或改革)的实质内容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平均地权为内容——“前五十年中经历三种政权,发生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则发生了三次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改革” 。
在漫长的上述近百年中,农村私有土地的流转,其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关系甚至影响了农民对自身的繁衍生息,关系甚至影响了农家的生存去留,关系甚至影响了农人的衣食住行,关系甚至影响了社会的变革,继而产生了有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兼并、垄断乃至导致社会体制大厦根基的松软,这成了百年中国的全部。严格地说,成了清末和大陆民国的全部。诞生、依托于江浙海洋财团的民国政权,对农民的漫不经心、得过且过和不对三民主义民生、民权、民治等在农村的表面化“贯彻”,也为自身政权埋下了颠覆的隐患。
尽管山西是全国的特例。当时的阎锡山山西政权,还吸引了北洋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睐,他们实施的“村本政治”,对农村和农人,给予了最大的眼球。各地到山西参观者络绎不绝,连吴佩孚都曾于1922年5月25日致电阎锡山表示钦佩之情:“年来国家多难,荼毒生灵。公独修明省政,保障三晋,树各方模范,已既成效昭著。深望扩充宏愿,利济国家,从解决之方,谋障碍肃清之计。”尽管这样,土地,依然是这块山水的全部。
他们失地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联系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的农村土地流转,不难发现,在这个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农村生产力低下导致的民生艰难和农民以婚姻后代繁衍为最重,是土地流转和失地的三个重要原因。
有幸发现,作为山西省壶关县店上村郝天成一家的30张地契、房契,其完整性、连续性、真实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清末、民国乃至建国初期土地房产流转的真实范本。
迁徙之后的生存
郝天成,本山西省屯留县东史村人氏。数百年前,大约是明朝末年清军入关时,郝天成祖上因反抗暴徒欺压,失手将其杀死。为躲避命案,跟随当时山东向山西的移民潮,从山东蓬莱迁徙到山西省屯留县定居,初次实现了人口的迁徙。
他们在屯留县东史村居留时,每逢清明节,还常常乘着夜色,离开此地的当中院,昼宿夜行,遁入山东蓬莱境内,在祖地为祖宗烧纸扫墓,寄托哀思。
到了清道光年间,迁居屯留已有数代的郝天成,身怀木匠技艺,孤身一人因故离开了屯留东史村“当中院”,辗转迁徙到本省壶关县店上村谋生。
店上村,成村于明朝中晚期,也可以说,在明朝二百七十年和清朝初期,正是店上村因店成村的“造村”时期。那时的店上村,远没有如今壶关县的林青庄村(古称林青里)闻名,仍是一个小交通枢纽边“歇脚”的多家路边小店。明朝所记录当地麻巷村大儒杜斅的籍贯,皆为林青里。
西去仅四十余华里的万里荫城,渐渐热起来的铁货,需要东至河南、山东、直隶的便捷运输通道——一条古代的简易“高速路”:荫城—柏林—谓里 店上—十里岭—京津冀鲁豫,店上作为当时的驿站或歇脚之地,应运而生。
郝天成及其儿子,参与主工修筑的店上村大桥,确证了店上村是当时交通的产物。也许因为修筑了大桥,店上村选择了郝天成,郝天成最终也选择了店上,定居于此。
“当中院”,作为迁徙中一个永远不能丢弃的符号、符咒和图腾,得到了永远的传承和体认。郝氏30张契约证实了许多财物的来历:如今的当中院,一百六十年前,原是当地郭氏子弟的产业。从契约中窥见,郝天成来到店上村,首先取得的是房产而非土地,证明了其作为工匠,在迁徙地由起始务工,盈余后转而务农的“农工”结合的生存方式。
分支繁多后,取得土地已经是第二、三、四代的事情了。他们通过艰辛的劳作,不断取得了房产和土地等生存资料。到第四代,已经繁衍男丁六支,成为乡村店上东头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家族。
商业,原本是郝天成念兹来兹不欲的生存依托。到民国后期,当后代已经发展成六代、七支,拥有土地数十亩、房产几十间的有产阶级时,当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村依靠土地收益的太行山区农村殷实富裕家庭代表时,他们依托店上的商业繁荣,买入和租用市面房舍,经商做买卖成为郝氏的又一个经营方式和不贰选择。商业,也是郝氏短期内成为店上望族的重要手段。从30份契约中可知,二代郝立忠、郝立孝已经置办了商业店铺,到了民国十九年,其子郝春山因经营不善,“困顿且无处起兑”,不得已又将店铺转让与侄儿郝海水经营。
这里,从郝天成及其后四代生息和拥有土地的过程透视,可以穿透清末农业经济的时空,看这一时段内地和北方的、封闭的山区农人的发展脉络。特别是通过他的第四代传人郝海水,从留存了他经营第一次交易土地的时间恰好是民国元年来看,他所经营的土地、房产的变化,我们真的窥见了当时山区小农经济中,惜地如金、勤于劳作的经营状况。
民国的政权、官僚如何实施对农商的治理?
“契纸费收据”、“指名喊控”、“索要钱项”、“限时办结”等等,均是清末民国对农户和商业实施管理的凭据。
30张契约使我们窥见了清末、民国和建国初期农村集镇经济中,展现的政权以及公务人员诚信、赋税、货币贬值、纠纷解决以及国家基层机关的办事效率、惩戒机制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民国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间经营往来、人情世故等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仔细地研究和借鉴它,将丰富我们对清末、民国乃至建国初期农村社会经济的认识,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和借鉴价值。
百年辛劳终显名
“黄金无根,偏长勤俭之家;丹桂有枝,独生书香门第”。这是郝天成在壶关县店上村第五代传人郝守信经常使用的春联书法词句。我国古代还有“门第常新,足照三槐之瑞;人文蔚起,高拔无桂之芳”,这也是旧时宗谱里常见的句子。
30张契约虽然没有记载郝天成及其后代在清末民国中的“科举”读书的实例,也许,正是郝天成后代积蓄足以开始耕读传家、科举进仕时,中国的科举业已寿终正寝。但是,从遗存祖屋的牌匾、砖雕等精雕细琢的情景里,我们开始体味到郝天成后代真正转轨“耕读传家”的有关事迹。
科举时代,“耕读传家”对农家具有巨大吸引力。“耕”是生存之本,“读”是进身之阶,是乡民攀登士族社会阶梯的唯一途径。著名古村落研究、保护专家陈志华教授对此深有体会:“看到古村落的义塾和书院,看到那巍然高耸的文昌阁和文峰塔,看到宗祠前为举人、进士树立的旗杆和村口的牌楼,看到住宅槅扇窗上精细的‘棋琴书画’或者‘渔樵耕读’的雕刻,你才真正理解农村的‘耕读文化’,理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在农村的重大意义。”在已逝去的年代里,耕读不仅仅是属于文化层面的田园牧歌,它是家族的头等大事,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涵。他们晴耕雨读,春耕冬读,秀者抱经,朴者负耒。众多寒门细族在这种耕读的秩序下崛起于阡陌陇亩之中。郝天成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在“当中院”的东南西北四面房舍的窗户上,都木雕有“滋兰香”“惟德馨”等词句。一般来说,刚刚迁徙到此的郝天成,如何生存下来,站稳脚跟是首要任务。只有生活初步安定,解决了衣食温饱,“读”的问题才会提上议事日程。黄仁宇先生指出:“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方式是一家之内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逐步上升到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
郝天成家族非常符合这条规律,他从贫民工匠到耕读传家再到店上望族,从修店上古桥、修筑当中院、开商铺,再到30张地契的签约。第三代孙郝银山曾是最勤俭的典范,是这个家族第一个吃不上盐而用沤制酸菜浆水膏代替、并把挑夫使用的扁担磨得溜光的人。可看出,这个家族生存、发展、升华轨迹的三座里程碑。
郝天成初创时期,只有店上当中院中的少数房舍。“上”在太行山壶关县语境中,是一个山区地理形势相对狭窄的处所,如淙上、寨上、东方上等村名。如今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后,后代中已有了15支,住处从“上”转移到壶关小盆地县城和上党大盆地长治市、晋城市乃至太原盆底居住的有21家。
考古成果表明,河流谷地、山间盆地对人类特别友好,最适合人类栖居。如果一个姓或几个姓的家族能够获得这样一方乐土,就可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躬耕不废课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圈、文化圈。日本学者上田信据此写成《传统中国:盆地、宗族所见之明清时代》一书。地因人胜,郝氏在壶关众多“上”中声名鹊起。且自1930年代末,郝天成第五代长孙郝守信从潞安师范毕业,并先后从壶关县牺盟会秘书、抗日县政府分管钱粮负责人的重要岗位上离职后,因想远离战争,选择了从教职业,他在山西省壶关县五集小学启蒙教授了山西一代书画大师李才旺和大庆油田分公司党委书记张银水;1956年郝天成第五代次孙郝福文考入国家重点院校 ——山西农学院;2005年第七代孙郝二伟在兰州市因获得全国物理竞赛前100名成绩,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2010年,免试进入中国科学院兰州核物理研究所工作。至2012年,郝天成子孙已有33位子弟考入国家院校,耕读传家成为现实。
我们的祖辈乃至父辈均生长并经历了民国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祖辈和父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随着他们的离去,究竟是亲切,还是敌视,抑或是留恋,乃至在特殊时期的“莫言”。应该说:他们,对于清末乃至民国,较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我们,有着无以言述的爱怨情仇。那是一段无法跃过的时空,也是镌刻了深痕印迹的时空。然而,这个时代,对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尤其是上世纪70后、80后出生的人,时代的远逝、宣传的含混,乃至民国之人作为活化石的渐渐离去,我们得到的民国,有很多猜测、臆想的成分。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停留在“金陵春梦”、“蒋家王朝”、“京华烟云”、“十里洋场”等表层的东西吗?特别是作为养育我们的土地 ——太行山晋东南的山地农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如果缺乏有力的佐证,我们不得而知。
这就是30张契约的珍贵所在。在它的解读中,一个完整的店上郝氏家族“耕读传家”的奋斗历程,将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左满明)